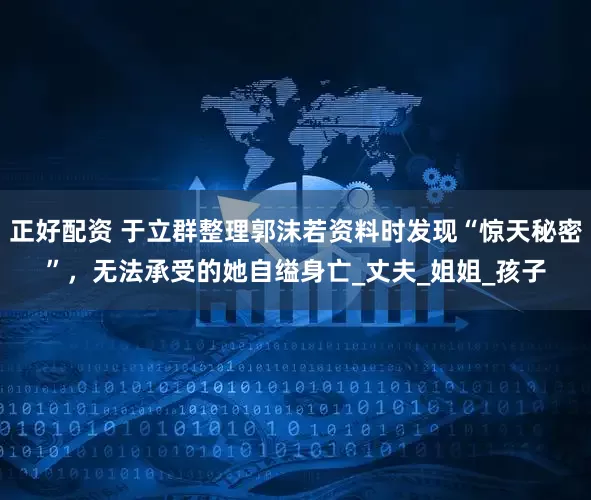
1979年初,北京的冬天特别冷。
那天晚上,于立群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手里拿着一封发黄的旧信。
她本来是在整理郭沫若的遗稿,那是她丈夫生前留下的一箱手写文稿。
她一直想着要替他出一本全集,把他的文化遗产完整保存下来。
可她没想到,会在一堆旧信里看到姐姐的名字,立忱。
那一刻,她整个人仿佛被冰冻了。
这封信彻底打破了她对丈夫的认知,甚至动摇了她一生坚守的“信任”。
她读完那封信,久久没动,直到炉火熄灭,屋内一片昏暗。
而这封信,最终把她送上了不归路。
展开剩余83%在很多人眼里,于立群只是郭沫若的妻子,但她可不是普通女性。
她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,祖上几代为官,母亲是两广总督的女儿,小时候家里虽清贫,但规矩森严,重教重礼。
她与姐姐于立忱感情极深,两人一同在上海接触新文化,接受教育,也投身时代洪流。
年轻时她参与话剧演出,后来成为中共地下文化组织的一员,还做过编辑、广播员,是延安文艺界里出了名的“女干部”,能写会讲,胆子大,也有主见。
1938年,于立群和郭沫若在武汉相识,那年她22岁,郭沫若46岁。
郭当时是延安请来的文化重臣,也是国民政府礼聘的大人物,头顶着“新文化运动代表”“古文字学大师”“诗人”的光环。
他看中了她的聪明和干练,她也被他的才华和声望吸引。
两人迅速走到一起,并于1939年结婚。
之后四十年里,于立群成了郭沫若最重要的生活伙伴、政治助手、文学秘书并且为他生下了6个孩子。
1978年6月,郭沫若因病去世,享年83岁。
在此后的几个月里,于立群强忍悲痛,着手整理丈夫留下的信件和文稿。
她本想用一套“郭沫若全集”来作为对丈夫的纪念。
在外人看来,她是个坚强的女人,操持葬礼、接待宾客、继续丈夫的学术事业,忙得井井有条。
可没人知道,就在整理文稿的某一晚,她翻出一封泛黄的信,是郭沫若二十多年前写的。
信中抬头写着“立忱”,多么亲密的称呼,让她的手指瞬间冰凉。
立忱是她的亲姐姐,一个她早已故去、心里始终怀念的人。
她小心展开信纸,一字一句看下去,越读越难以呼吸。
那是郭沫若写给她姐姐的情书。
字里行间写着深情、依恋、愧疚,还有“未竟的愿望”。
于立群这才意识到,郭和姐姐之间不仅有过亲密的情感,可能还有未出生的孩子,甚至曾私下有过成婚的想法。
于立忱1937年突然自杀,家里当时没人细问缘由,只说她“病情恶化、情绪低落”。
那年她才二十多岁,美丽聪慧,活泼灵动。如今看来,也许这段感情是压死姐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而一年后,郭沫若娶了于立群。
自己丈夫跟姐姐的过往,她从未听郭说起半句。
她一直以为,自己是郭沫若真心喜爱的女人,可现在看,她更像是丈夫感情上的慰藉品。
于立群这一生,为郭沫若付出太多太多。
她为郭沫若生了六个孩子,几十年里照顾家务,上下打点,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这个男人。
即使是家中两个儿子相继去世,她身心俱疲,胃病缠身,也还在强撑着操劳。
“家是我的阵地。”她曾对友人说,“老郭的事情太多了,我得帮他。”
她曾在一次日记里写:“六个孩子,四个还小,晚上不睡,白天照常工作。苦,但值得。”
郭沫若常年忙于学术与社会事务,几乎不管家里的事情。教育孩子、赡养老人、家中亲友照应走动,全靠于立群一个人。
很多时候,她还要维护丈夫与外界的社交,有人来求字求情,她得应对得体。
在郭晚年生病期间,所有医院安排、治疗计划、生活起居都由她一手安排。
1979年2月25日,于立群在家中自缢,终年63岁。
她没有留下遗书,也没有任何只言片语。
外界只知道,她情绪低落,精神状态不好,有“抑郁症倾向”。
可熟悉她的人都明白,她的自杀不是冲动。
她不是一时想不开,而是因为她终于明白,四十年的婚姻原来也只是个“代替品”。
她全心全意爱了这个男人半辈子,可他连最重要的往事都从未对她提起。
她到最后都没有控诉什么,只是在最安静的方式里,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
只留下一封信,以及一个让后人无法释怀的问题:
郭沫若,真的值得她为他耗尽所有,甚至连命都搭进去吗?
郭沫若一生有三任妻子:
第一任张琼华,是包办婚姻。婚后没几天他就离开赴日,张琼华在乡下一等几十年,孤独终老。
第二任是日本女子佐藤富子,为他断绝亲情、生育五子,最后被留在日本,儿子靠自己奋斗考上东京大学,终生没能再见父亲。
第三任是于立群,革命战友、贤妻良母,陪伴他半生,最终也抑郁而死。
他爱的是谁?
或许,正如有人评价:“他最爱的,是他自己。”
发布于:北京市新玺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